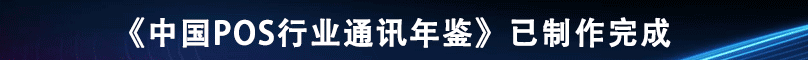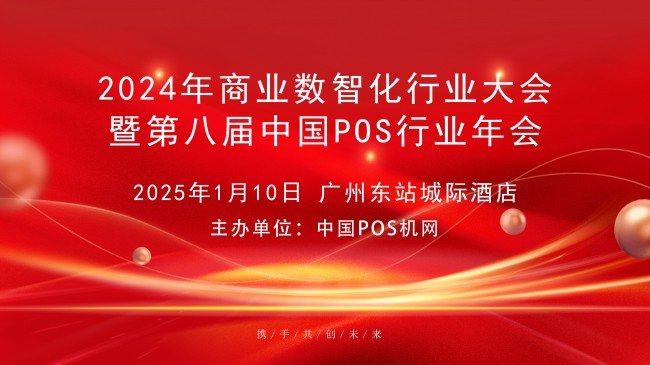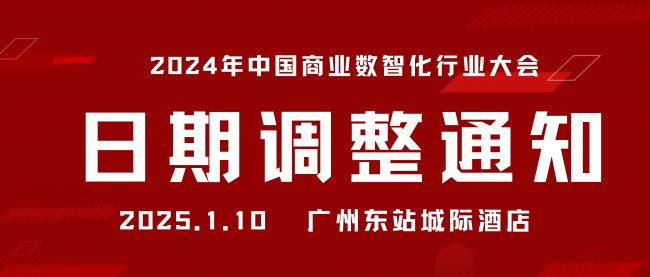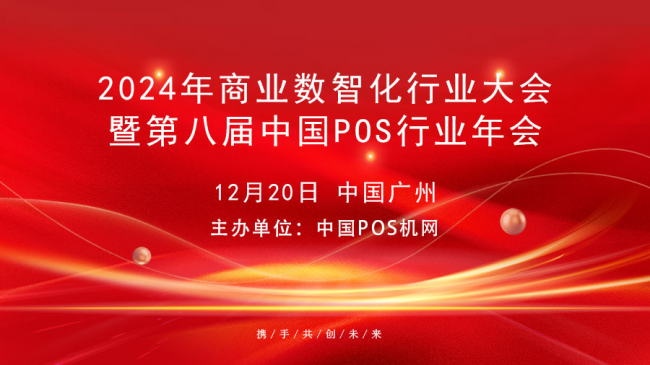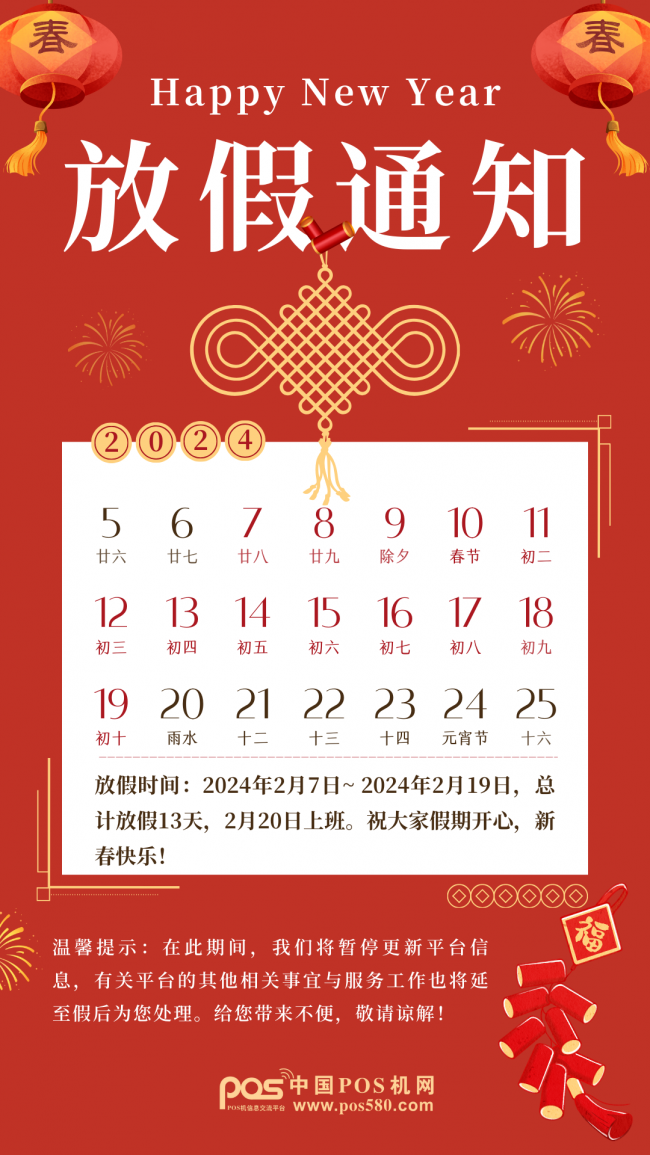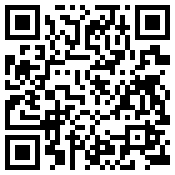自從時文朝上任銀聯總裁之后,他的每次內部講話都倍受市場關注。通過講話,他不僅向銀聯員工傳達了改革發展的信息,也同時給外界提供了了解銀聯戰略思路的線索。《財經》記者獨家獲悉,在2014年年終歲尾之際,時文朝又在銀聯內部發表了題為《不一樣的新年、不一樣的銀聯》的新年致辭。
在這份致辭中,時文朝稱,銀聯正處在“卡組織六十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不能否認的是,銀聯原有的平臺價值逐漸減弱,有被“過頂長傳”、淪為通道的風險。
但,危機就是轉機。時文朝提醒銀聯上下牢記“忘記終端將終遭離棄”這個道理,需要從應用場景入手幫助其所服務的機構提高終端用戶黏性。
銀聯在這個過程中也需要重新尋找它的平臺價值。時文朝說,本著開放的原則,銀聯不會去做商業,而是要為商業提供更好的支付服務;銀聯做的甚至不是支付本身,而是更好地“服務于支付”,乃至使服務和支付更好地整合。
附:銀聯總裁時文朝內部新年致辭:
不一樣的新年,不一樣的銀聯
時光荏苒,我們又迎來了新的一年。值此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際,我代表中國銀聯黨委和經營班子,向長期關心、支持銀聯發展的各級政府、監管部門、股東單位以及所有銀聯卡合作機構、商戶、持卡人送上新年的祝福,向銀聯系統全體同事及家人致以真摯的問候!
先民如此布置下新年時間,無疑是為了讓我們在冬的最深處,瞭望春的到來。恰似紛擾有時的支付產業,既熱鬧紛繁也寒意料峭。對銀聯而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無疑也是一個最危險的時代……無論眾人如何評說,我們終歸要正視這個完全不同以往的年代。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急速變化的年代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無人有權心存僥幸。
(一)卡組織六十余年未有之大變局
一切邏輯,都要從根上進行推演。對銀聯而言,這個根就是“卡組織存在的根本價值是什么”。
卡組織或者說“四方模式”卡組織,通過整合發卡、受理兩端的眾多機構,建立統一的系統、標準、規則、品牌,最終為持卡人、商戶提供支付服務。因此,舉凡卡組織皆以“平臺”自命,究其根源就在于其產生、發展的最大價值就在于解決了平臺兩端機構的協調、談判成本。
在卡組織濫觴之地,美國的銀行數量高峰時曾達到18000多家,即使目前也保有6891家(2013年第三季度FDIC數據)。這種環境,是四方模式卡組織產生的天然土壤。因為即使強大如花旗、摩根大通、美國銀行等也無法挑頭協調全部銀行,任何一家銀行要發行一張在全國通行通兌的銀行卡都是無法完成的任務,其間的協調成本、談判成本非常巨大,同質化機構的利益沖突更是無法逾越的障礙。正是在此產業環境下,歷經多年美國本土有且僅有兩家四方模式卡組織巨頭,其他組織在巨大的交易成本下或無容置喙,或另辟蹊徑。無疑,發卡與收單的高度離散狀態,是四方模式卡組織產生并稀缺的決定性條件。
雖然市場紛紜,言必稱“平臺化”,但真正的平臺經濟無疑要同時體現出兩大特征:“輕資產”與“重關系”。資產輕,是因為平臺的重點在于整合,真正的生產與服務大部分并不是由自身提供,因此無需過多依賴硬件的持續投入;關系重,是因為平臺的難點也在于整合,協整上游分散的生產、服務能力,滿足下游海量的終端需求,制定規則、統一標準、建立品牌,這里的“規則、標準、品牌”都須經協整上下游方可建立,因此“關系”不可謂不“重”。以此標準望去,凡客誠品[微博](垂直電商)像是一種平臺,它不生產襯衫,它只是“襯衫的搬運工”;小米手機[微博](軟硬件整合商)像是一種平臺,它沒有工廠,卻能找到最優質的硬件、最好的廠商做出好手機;易到用車(用車平臺)像是一種平臺,它不擁有哪怕一臺車輛,但卻可以讓用車需求更快捷地實現匹配;COD平臺像是一種平臺,它沒有貨柜、倉庫和車輛,卻全程貫通了物流、倉儲的信息流……因此整合者是平臺的首要標簽,重關系才是平臺的真正價值所系,輕資產只是平臺模式優越性的一種結果。
——信息的集聚、交易的集中、成本的降低,用經典教科書理論詮釋,雙邊市場的價值就在于解決信息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問題;而如果交易成本不存在,或有更可行的手段解決交易成本問題,平臺就需要尋找新的存在的意義。
回頭看銀行卡產業,四方模式卡組織同樣也是典型的平臺,它不發卡也不收單,但它的存在能夠讓發出去的卡更好、更廣泛地實現受理,繼而發出更多、更好用的銀行卡。但是,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前提是前述的“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市場對“重關系”的整合者的需要。
中國現在的環境是:發卡機構408家(全部是銀行),POS收單機構265家(219家銀行),前五大發卡機構的市場份額達70%,前十大收單機構的市場份額達73%,而且集中度日趨提高。相較于6891家機構相互談判,百家機構相互談判的交易成本根本不是一個量級,且在如此高的集中度下,實踐中談判桌前的主角一般就只會剩下發卡、收單兩側TOP10機構。至此,從成本上,一個“發卡-收單”直連的網狀模式,已并不比“發卡-卡組織-收單”的星狀模式高太多,一家機構建立與發卡、收單某一側或兩側的通路的難度也大幅度降低。
至于技術,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可慮的只是市場啟動階段,當平臺兩端的參與機構稀少,市場培育受限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沒有足夠好的受理環境,沒有人愿意發卡(持卡);沒有足夠多的人持卡消費,沒有人會愿意對受理環境進行投資。這個過程漫長且耗資巨大,單方面的投入都不經濟,因此整合者的價值就在此刻得到了最大的彰顯,可以說,正是整合者締造了市場。但是,如前所述,在此之后平臺的價值就與市場集中度緊密相關。
基于此,我們也許可以總結出中國銀行(4.15, 0.21, 5.33%)卡產業的歷史與現實:聯網通用,是產業發展的上半程;當發卡規則、受理環境、用戶習慣等市場要件構建完畢,產業發展進入了下半程,此時平臺的協調價值基本完成大半,“平臺化”的價值將不斷下降, “通道化”就成了現實而又迫近的風險——更嚴重的是,權益保護乏力甚至缺位的環境又使得風險大大加劇。
當前市場亂象,或許一半根源于此。
(二)被旁路的沖擊
被沖擊的不僅是卡組織,還有整個產業。
如前所述,高度集中的市場,一家機構可以很輕易地建立與發卡、發單機構的全網通路。建立之后,“通道化”的風險其實并不僅限于銀行卡組織。在過往沸騰的廿年里,IT業沖擊傳統經濟很重要的一個模式就是所謂的“OTT(即Over The Top)”,籃球界稱之為“過頂傳球”,在互聯網領域則指服務提供商旁路了運營商網絡,直接面向用戶提供服務,運營商淪為單純的傳輸管道,管道中傳輸的巨大價值逐步游離于運營商。正如Skype、微信顛覆語音通訊,旁路電信運營商,線上支付機構也將改變支付市場,在監管政策沒有顯性化時,也許有一天直接貫通發卡、收單,建立從用戶到商戶的全鏈條,最終旁路傳統金融機構。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網絡支付業務150億筆、10.3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8.5%、143.8%,增速已分別是銀行卡跨行交易增速的2.6倍和4.3倍,新型支付工具對傳統銀行支付工具的替代效應日益明顯,而卡、存折、支票……正是這些工具構成了傳統零售銀行的基礎。
銀行業務的本質是存、貸、匯。匯即支付,是一切經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匯的旁落無疑是整個沖擊和沉淪的開始。
相較于銀行,大多數非金融支付機構更感生存壓力。微利,一直是中國支付產業顯著的特征。收單銀行可以寄望于存款帶來綜合收益,而非金融收單機構則只能在“追求規模效應--惡性競爭、違規經營--拉低整體費率--更加迫切地追求規模效應、惡性競爭”的循環中逐漸沉淪(也可預見,一場席卷全行業的大規模兼并重組必在醞釀)。在這種環境下,當新模式橫空來襲,發卡側尚有賬戶這一核心資源可以堅守,收單側則將徹底被“過頂傳球”,無力阻止商戶的紛紛離棄,已是微利的收單機構又如何能夠抵御敢于“燒錢”的互聯網公司!而線上、線下二元價格體系,又將把這種空襲真正變成了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有人說,受理環境改造,機具投入巨大。其實,硬件投入構不成收單機構完整的“護城河”。互聯網最擅長的就是“硬件軟(件)化”,充分利用現有技術條件,以此擺脫對硬件的依賴。二維碼、聲波等等執行的不正是這種思路?
——以上并不是對現實無來由的危言,也不是對未來的悲觀預測,而是整個產業目前實實在在正在發生和即將要發生的故事。
(三)忘記終端將終遭離棄
沉淪從哪里開始,救贖就要從哪里而起。
在市場高度集中的情況下,銀行卡組織要想提高平臺價值,就必須為兩端的發卡、收單機構提供除了聯網通用以外的新價值;整個產業當下最大的困境是被旁路的風險,突出表現為用戶的離棄,因此幫助他們留住最終用戶是發卡、收單機構最需要的價值。無疑,答案指向了最終用戶!
支付產業的最終價值來源于消費者(持卡人)、商戶。這是兩組更加海量、離散的群體,終端需求復雜而多變。如果將“平臺”的外延從銀行卡組織推展至整個銀行卡產業,持卡人--發卡--卡組織--收單--商戶,我們可以發現“交易成本”的問題和“重關系”的整合者價值依然存在!
日常生活中,幾個典型場景:
場景一:你可知道你的銀聯白金卡在上海地區每月可免費代駕6公里?你可知道你的招商銀行(16.59, 0.91, 5.80%)信用卡有每周三美食可享五折優惠的權益?你可知道你的民生銀行(10.88, 0.10, 0.93%)信用卡有豐厚的加油、洗車、道路救援權益……坦率說,即使身為卡組織負責人,我也無法一一細說眾多信用卡行與行之間、普卡和高端卡之間在權益上的差異細節,更遑論普通持卡人。實際上,每年各信用卡中心打造“持卡人忠誠度計劃”都耗資甚巨,總體并不遜于“打車大戰”的燒錢規模,但苦于認知度不高、轉化率低,個中原因正在于缺少與持卡人面對面互動的“入口”。手機銀行App也許是個答案,但難道讓持卡人一家銀行裝一個App嗎?由此就帶來一對矛盾:消費者苦于無法管理(享受)卡片,銀行苦于無法推介自己。
場景二:在新經濟浪潮中,一些無力“觸網”的商戶顯得尤為落寞。比如那些“卷閘門里的企業”,電商化既無實力也不經濟;又如那些不適宜在線上銷售的商戶,因為物品可以通過物流抵達,服務則只能到店享用,看起來像是沒有電商化的基礎。但是,在信息化的大潮中,這些商戶同樣也有強烈意愿讓自己更直接、更迅捷地接觸消費者,不至于在全民觸網的時代中掉隊。于是,O2O模式成了這些小小微、海量、分散商戶的重要機會。近年來,利用UGC方式迅速崛起的互聯網公司,其廣受追捧的原因就在于成功解決了商戶與消費者信息交互的“入口”問題。
場景三:支付的升級能夠帶來效率的躍升,例如ETC通行能夠大大縮短收費長龍。但是,有時效率的瓶頸并不在于支付本身,而在于支付的前序服務的梗阻,例如就醫時的反復掛號、反復排隊、反復繳費。在這種服務與支付具有“高粘合度”的場景下,消費者需要的不僅僅是支付或服務的單一品類,而是“服務+支付”整合后的綜合體驗。
——請讓我們不僅僅從產品經理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場景,而更加概念化地去理解我們產業的終端用戶:場景一代表著銀行與持卡人雙邊整合的需求,場景二代表著商戶與消費者雙邊整合的需求,場景三代表著持卡人對綜合支付服務解決方案的需求。因此,當我們瞄準終端用戶,在銀行卡產業從offline到online的艱難跋涉中,可以發現的拓展方向包括但不僅限于此,但歸結起來可以說:在金融行業,得賬戶者得天下;在互聯網時代,得入口者占先機。如今,是把這一切都整合的時候了!
(四)“新競-合”的內涵與邊界
在這里,不得不提卡組織的定位問題。
卡組織不是支付公司,不做發卡、不做收單,“我的客戶只是銀行(機構)”、“通過服務銀行(機構)服務好持卡人、商戶”,保持超然、獨立的地位,超越各同質機構之間的利益沖突,本質上是為減少交易成本而服務。世易時移,卡組織依然要保持超然、獨立的地位,仍然要避免與體系內機構發生利益糾葛,只是在新的時代下它解決交易成本的視角已從發卡、收單外延到了持卡人、商戶——在這里,發卡和收單機構雖相對集中但卻各自為戰,持卡人和商戶更是海量且高度離散。
新形勢下卡組織依然堅持不做發卡、不做收單,只是要在謹記“我的客戶只是銀行”的同時不忘“我的用戶是持卡人、商戶”;要從單純“通過服務銀行服務好持卡人、商戶”向既“通過服務銀行服務好持卡人、商戶”又“通過服務持卡人、商戶服務好銀行”兩者兼有的方向進行轉化。
不僅如此,在提供綜合支付解決方案時,我們也會“積極有為”并“有所不為”,核心要義是“開放”。我們將服務(醫療、教育、旅游、公共交通、物流等)和金融、支付進行整合,但并不越俎代庖。有一天,我們也可以聯合合作伙伴(銀行、收單、互聯網企業、電信運營商等)推出類似HealthKit、TravelKit 、HomeKit等接入工具,為初次觸網的商戶提供所謂的Starter Kit,通過開放接口讓盡可能多的各行業參與者投入進來,讓前端的服務盡可能地專業化、多樣化、個性化,構建“商業運營--交易場景--支付完成”完整閉環,而我們依然“大隱于市”專注轉接清算,讓金融支付的支持更集中、安全、便利。前期,我們在線上支付推出的SDK開發者軟件工具包,就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定位在支付服務而不涉其他,可能會一時寂寞但終將絢爛。
例如,我們不會親自去做電商,雖然交易場景的構建對用戶黏性確實至關重要。因為沒有一家電商會將自己的后臺無保留地交給同質機構旗下的支付工具。客戶資料、交易流水等關鍵信息的流失,以及隨時在交易后“卡脖子”的風險,使得小電商們即使一時委身也終將尋機逃離。究其根本,商業追求的是“贏家通吃”,最好市場上就此獨家;支付追求的則是開放、包容,接入電商種類越多、支付工具的價值越高。獨占性與開放性的矛盾,所謂的“生態”終有到頭的一天。
總而言之,我們不會去做商業,而是要為商業提供更好的支付服務;我們做的甚至不是支付本身,而是更好地“服務于支付”,乃至使服務和支付更好地整合。
今天,越來越多的商業企業(無論線下巨頭還是線上電商)在申請第三方支付牌照,正是對前述構建能夠自我掌控的支付管道的防御策略的積極實踐。這就意味著,超然、獨立、“不做支付而服務于支付”的我們,在線上作為整合者無疑將存在著眾多的合作對象,存在巨大的價值空間。德不孤,必有鄰。
當然,如此小心翼翼地拿捏自身的定位,在“新競-合”關系下帶來的空間里顯得不夠高端大氣,但這是必須的!迄今為止,中國市場上能與各類主體開放合作而不觸及各自核心利益的,我不能說只有銀聯一家,但銀聯肯定是一家。無論是傳統的發卡銀行、收單機構乃至迅速崛起的互聯網支付機構,轉接清算從來都不構成他們的核心利益,更非專注前端服務的他們的比較優勢所在;而核心賬戶與沉淀資金的爭奪,也從來不在銀聯的字典里。因此,輿論的故事會里相互對立的劇情,雖然抓耳好聽卻不完全屬實。如今,兼容“為”與“不為”的定位,就是要服務好一切愿意加入到平臺中的主體:持卡人、商戶、發卡銀行、非金融收單機構、互聯網支付企業……更是對這種真正兼容并蓄、解決多邊交易成本的平臺屬性的全面升華和揚棄。
重申一遍,未來我們的服務將超越支付,這是因為我們開放;但我們的定位始終還在支付服務(乃至轉接清算),這是因為我們超然。新形勢下,這就是我們服務的內涵與邊界。
(五)寄意寒星荃不察
如果那山不向我們走來,就讓我們向大山走去。
身處變革中心,外界都在看著我們。當真的“狼來了”的時候,許多人都在問我們是否擔心害怕;坦率說,沒有壓力是不可能的,但憂讒畏譏、逡巡不前肯定不可取,直面挑戰是唯一選擇。如果外部壓力能夠倒逼我們內部改革成功,甚或是一大幸事;如果新進入者能夠為市場帶來新氣象,為民眾福祉增進做出貢獻,我們更加樂見其成——有人說,動輒千億萬億市值的任性土豪們,意欲闖入這樣一個微利的行業,看上的絕不是我們不到廿億的利潤。雖然他們所圖者大矣,但如果他們愿意并努力在這個需兼顧公共服務、信息安全和市場服務的領域有所作為,或愿與銀聯同道攜手,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產業帕累托改進,實是銀聯之幸、產業之幸、社會之幸,我們不僅樂見其成更要躬身學習。
成立十二年,始終與競爭同行,方有今天遍及148個國家和地區的網絡;始終向先進學習,方有三色標躍居世界第二、“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榮譽和希望;始終深耕廣袤大地,在紛擾的產業里做不彰顯的努力,才有現在45億張銀行卡和47.7%的滲透率,才能在十二年里完成從“現金+存折”向“現金+銀行卡”的快速過渡,提高貨幣流通速度,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活躍國民經濟。相信,我們曾經創造過歷史,我們也終將繼續創造歷史!
寥寥隨筆,寄語未來,并不想說多少戰略,更想研究一些具體的問題。未來千頭萬緒,一切都需從小做起、從現在做起。
祝福2015,祝福新的銀聯,新年、新事、新氣象!